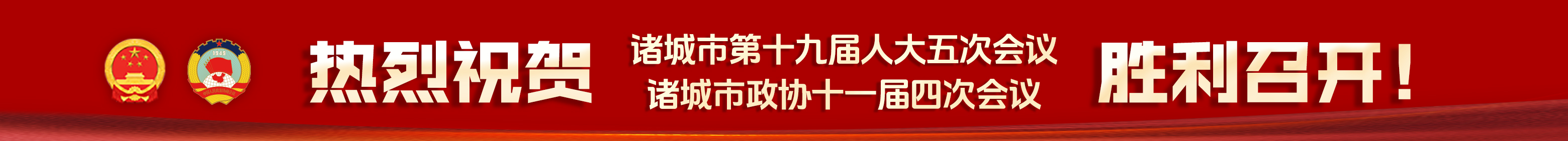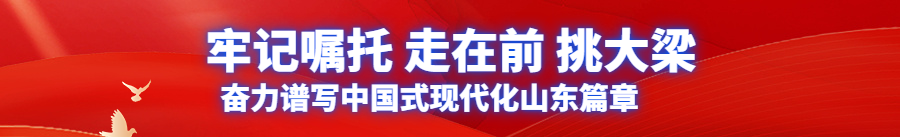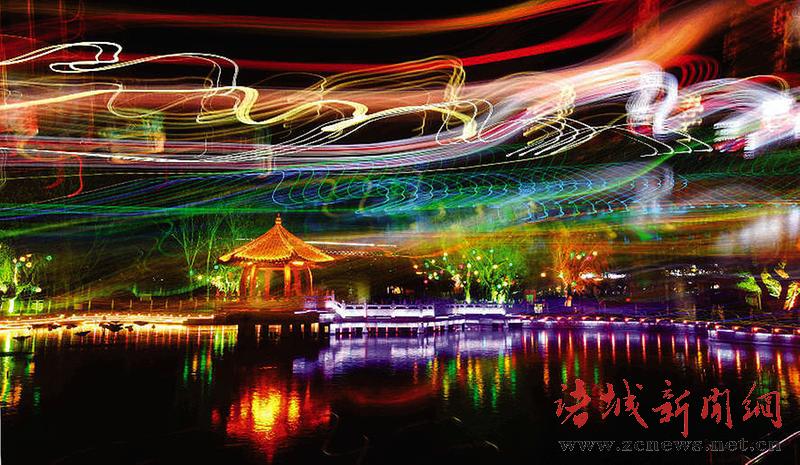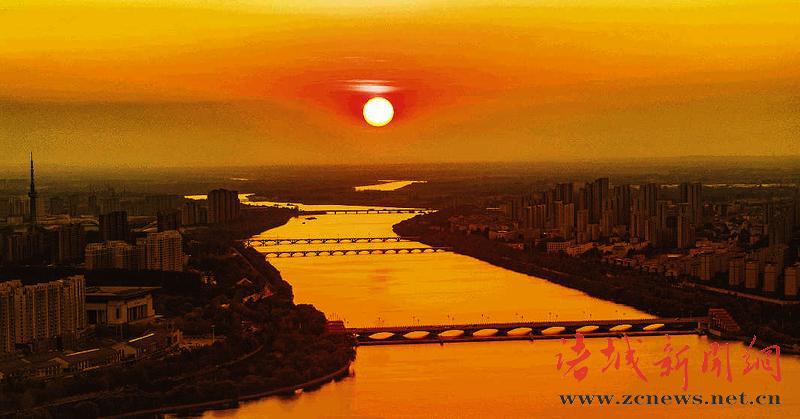父親經(jīng)常會俯身大地,努力耕耘,。在風(fēng)調(diào)雨順的日子里,,全家老少吃飽穿暖,身體健康,、強(qiáng)壯是父親的希望,。
由小麥到饅頭,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走進(jìn)了我們的一日三餐,,所以我特別珍惜今天的豐衣足食,。無論離家多遠(yuǎn),無論身在何處,,只要到飯點(diǎn),,我仿佛都能聞到饅頭的馨香,。
從每年的秋收之后,,十月一左右,小麥的種子就在泥土里發(fā)芽,,成長,。直到來年的芒種時節(jié),端午前后的收割,,小麥完成了歷經(jīng)嚴(yán)冬,、春寒和夏烤的考驗,最終顆粒歸倉,。
新收的小麥,,要進(jìn)行完一個隆重的儀式,我們才能享用,。在我們這兒六月六之前要上新麥子墳,,就是用新麥子饅頭去祖墳上先祭拜、供祖,。母親會用一個大三盆倒上小麥,,用水淘洗,再用干凈的包袱把麥子外皮的水擦干,,放在一張不用的大炕席或薄膜上曬干,,到村里的磨坊磨成面粉。做饅頭是母親的拿手活,,母親用大八印鍋蒸的饅頭,,松軟適中,我百吃不厭,。
天天吃上白面饅頭,,是祖輩和父輩們的夢想,。在缺吃少穿的年代,父輩們吃了不少苦,,遭了不少罪,。我們今天的美好生活是他們夢想實現(xiàn)的見證。
記憶最深的是母親過年做饅頭,,用老面做面引子,,揉成一塊一塊的面團(tuán),發(fā)酵,,再分成饅頭大小,,經(jīng)過反復(fù)搓揉,做成饅頭,。
我能天天吃上饅頭是在一九八五年上高中時,,那時我們都在學(xué)校投糧寄宿,每月二十八斤糧,。一天一斤糧對我們女生來說還行,,男生往往餓得晚自習(xí)后找我們女生的課桌洞,希望能找到我們吃剩下的饅頭,。記得有一次晚自習(xí)后,,幾個男生沒有找到饅頭,發(fā)現(xiàn)了一個女生課桌洞里有一瓶益母草膏,,還有滋有味地嘗了嘗,。那時候,我們每星期五下午有兩節(jié)勞動課,,老師會把我們分成幾組,,有打掃衛(wèi)生的;有去學(xué)校操場邊的小菜園拔草的,;有去食堂幫著蒸饅頭的,。我們都愿意去食堂幫工,食堂的老師有時會給我們點(diǎn)好吃的打打牙祭,,幫完工還能給我們幾瓣大蒜或幾塊咸菜,。食堂里蒸饅頭的蒸籠很大,一次放好幾層,,全用機(jī)器和面,,做饅頭,我們的任務(wù)是把從機(jī)器出來的長條形的饅頭板板正正地放在圓形的大蒸籠里,。每個饅頭二兩半,,一天一斤饅頭。我的安排是這樣的:早上二兩半,中午半斤,,晚上二兩半,,中午吃不上剩點(diǎn)晚上吃。我們吃飯用飯票,,值日生輪流負(fù)責(zé)全班同學(xué)的喝水吃飯,。每班一個竹片編的盛饅頭的大筐,一根扁擔(dān)和兩個水桶,,兩人一組打水,,兩人一組打飯。有一次輪到我和同桌去抬回饅頭筐,,分完了同學(xué)們的饅頭,,我的沒有了,就坐在課桌旁哇哇大哭起來,,把同學(xué)們嚇了一大跳,,生活委員李月亮趕緊拿了自己的饅頭給我送了過來。
我蒸饅頭是在參加工作成家之后,,工作之余,,我們閑聊,不知誰先扯到蒸饅頭上,,我們幾個女人的笑聲傳出老遠(yuǎn),。邵大姐第一次蒸饅頭沒等面發(fā)蒸成了石頭疙瘩,被她對象用包袱背回了娘家,,還說是閨女孝敬老娘的;李大姐第一次蒸饅頭面軟了,,從蒸籠的縫里掛起了面條,;張大姐把饅頭蒸糊了……
那天晚上,我做了一個夢,,夢見娘在灶臺蒸饅頭,,我叫了聲娘,娘像沒聽見沒回應(yīng),,我大聲叫了一聲,,夢醒了,隱隱約約感到肚子有點(diǎn)餓,。想娘了,,想吃娘蒸的饅頭了。
劉明芬 (作者系山東省散文學(xué)會會員,,諸城作協(xié)會員)
1 條記錄 1/1 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