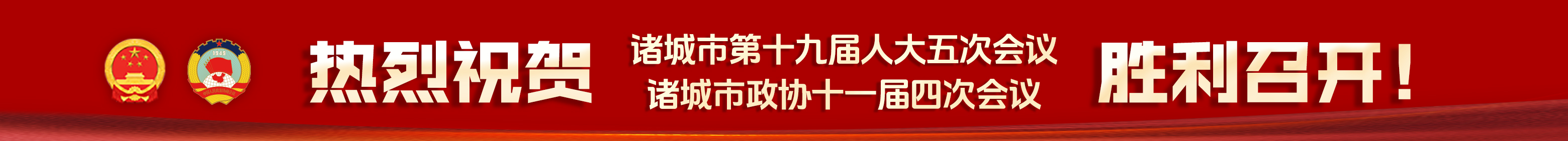劉景森
過了臘八就是年,。
每年的年味都是從臘八節(jié)逐漸濃烈的,每年的年味都是從農(nóng)村年集開始蔓延的,。春聯(lián),、年畫、紅燈籠,,把大集渲染成喜慶的大紅色,;鞭市上傳來零星噼啪聲,伴著陣陣硫磺,、硝煙的刺鼻氣味;賣豬頭,、豬蹄,、豬下貨的,賣粉條,、粉皮,、豆腐的,,賣蓋墊、笤帚,、炊帚的,,叫賣聲此起彼伏,鄉(xiāng)音依舊那么親切,。老少爺們把年味裝滿三輪,,興沖沖地帶回了各自的村莊。
我更懷念小時(shí)候的年味,。
小時(shí)候,,進(jìn)了臘月,父親會(huì)去趕集稱上幾斤舊報(bào)紙,,然后請(qǐng)位村里的手巧之人,,父親打著下手,把原來扎的福棚,、墻面再重新糊上一層報(bào)紙,,那些被灶煙及煤油燈熏黑的福棚、墻面頓時(shí)變得潔凈亮堂起來,。除夕那天,,用圖釘把墻上貼上幾張從集上揭的新年畫,再把我們兄妹仨掙的三好學(xué)生獎(jiǎng)狀整整齊齊貼到最顯眼的位置,,以便于親朋好友來拜年時(shí)及時(shí)諞拉一番,。
上世紀(jì)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,我家貼的春聯(lián)大都是青心三哥親手寫成的,。三哥是師范畢業(yè)生,,琴棋書畫樣樣精通,當(dāng)過幾年老師,,后來因受家庭拖累,,辭職回村務(wù)了農(nóng)。三哥與我血緣關(guān)系并不近,,已是出了五服的兄弟,,但他與我父親私交甚好,過了小年,,他就主動(dòng)打發(fā)女兒來我家要去對(duì)子紙,,寫好、晾干后再送回來,。
母親在為識(shí)字班時(shí)在村里成衣鋪里做過裁縫,。臘月初,母親就會(huì)找出費(fèi)事巴力攢的幾塊錢和幾尺布票,,去門市部扯幾尺布,,裁好,,坐在縫紉機(jī)前,嗒嗒嗒地親手為我們兄妹仨每人做一身新衣服,。出門拜年前,,我們穿上母親做的新衣,沒有想起那首“臨行密密縫,,意恐遲遲歸”的古詩,,只感覺自己好像比平時(shí)俊了許多。
年五更那掛鞭炮,,我只負(fù)責(zé)挑著竿子,,父親負(fù)責(zé)點(diǎn)燃,噼里啪啦的,,威力極大,,放完鞭炮,祭拜天地神仙之事(老家叫發(fā)紙馬)才算禮成,。記得有時(shí)姥爺會(huì)給我買一包拉爆仗,,兩手一拉,啪地一聲脆響,,威力很小,,安全,但從中找點(diǎn)過年的樂趣還是綽綽有余的,。
待父母發(fā)了紙馬,,合家吃了過年餶餷,天還烏黑烏黑的,,這就要出門拜年了,,過去有起得早過得好的說法。街上隨之喧鬧異常,,那時(shí),,人們以拜年的隊(duì)伍壯大為榮,說明戶門大,,嘎呼得怡和(huo,,和諧之意)。輕輕道一聲“嫲嫲爺爺過年過得極好”,,嫲嫲爺爺總是及時(shí)回一句“您起得挺早哈”,,老嫲嫲小心翼翼地從席底下找出兩毛壓歲錢,分給小孩子,,頓覺有種大發(fā)橫財(cái)?shù)暮〞沉芾臁?br /> 年后,,姥娘門前看大戲,夏家營(yíng)子茂腔劇團(tuán)咿咿呀呀唱起了《卷席筒》《墻頭記》,再后來就是背起箢子(箢子里盛上二大大炸的香油果子)出門兒去看七大姑八大姨,,直到吃了元宵、放完滴滴錦才算過完年,。
如今,,年味漸淡,盡管如此,,居在老家的父母仍照例蒸上幾鍋菜包,、豆包、面魚和餑餑,,當(dāng)它們士兵列隊(duì)般被擺在炕頭上等待上鍋時(shí),,我們總算找回了一點(diǎn)久違的年味。這些面食將是年后裝滿后備箱的濃濃親情,。
因疫情原因,,學(xué)生早早放假了,教師依然堅(jiān)守崗位,,批卷,,培訓(xùn),聆聽專家報(bào)告,,幾天下來,,繁忙的工作才暫告一段落,老師的假期才真正開始,。
與此同時(shí),,年,悄無聲息地向我們走來了,。
(作者系濰坊市作協(xié)會(huì)員,、山東省散文學(xué)會(huì)會(huì)員)
1 條記錄 1/1 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