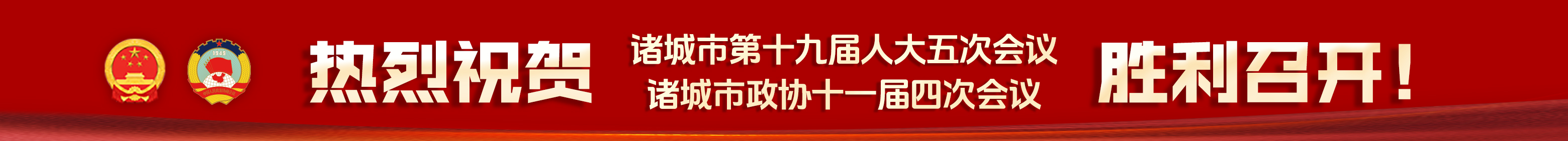孫愛勛
“八月剝棗,,十月獲稻”,,秋風(fēng)過處,棗兒熟了,。
院里的老棗樹是爺爺種下的,,現(xiàn)在已有合抱粗,樹干粗糙皴裂,,有的地方還長了青苔,,有歲月久遠(yuǎn)的滄桑感。
棗樹向墻外傾斜著身子,樹冠碩大,,伸在了墻外,。秋風(fēng)送爽,上搭下掛的棗兒熟了,,紅的,、半紅的,青白的,,熙熙攘攘,,挨挨擠擠。父親坐在樹下的板凳上,,吸溜吸溜吸煙,,隨后抬頭望望棗樹,自言自語說:“該落棗了,?!?/p>
晴天麗日,父親扛著竹竿,,來到院墻外的空地上,我挎著提籃,,尾隨其后,。長竹竿在樹枝間來來回回?cái)[動,棗子稀里嘩啦落下來,,“大珠小珠落玉盤”,。我蹲在地上,一顆顆撿,,棗子落在頭上,,咚咚敲著,生疼,。
村里的孩子圍過來看熱鬧,,吧嗒著嘴,饞涎在嘴里打旋兒,,但沒人去搶拾,,站在邊上,眼睛滴溜溜轉(zhuǎn)著,,看我和父親在棗雨里手忙腳亂,。
棗子落得差不多了,父親停下來,,蹲在地上吸一袋煙,,煙霧繚繞著父親的臉龐。
父親吸過煙,伸個(gè)懶腰,,拿過提籃,,從邊上的第一個(gè)孩子開始,一把把棗子,,把他們所有口袋塞滿,,看著孩子們高興的遠(yuǎn)去了的背影,父親自言自語說:“東山家的孩子又長高了,?!?/p>
落下來的棗子,父親沒有拿到集市上賣掉,,用笸籮盛著,,送給了左鄰右舍和親朋好友,剩下的,,母親用針線穿起來,,吊在堂屋門前的鐵橛上,曬干了,,過年的時(shí)候做棗餑餑,。棗餑餑是一種花式饅頭,盤花打結(jié),,上面插滿了棗子,,如春花盛開,似繁星滿天,,既悅目,,又美味。
有年秋天,,我去山洼小學(xué)代課,,因離家遠(yuǎn),就住在了學(xué)校,,星期天沒事,,去大山里轉(zhuǎn)悠,在一溝畔,,看到一棵快要落盡葉子的酸棗樹,,上面掛滿了密密麻麻的酸棗果,通紅通紅,,瑪瑙一樣吸人眼球,。我蹲下去,一顆顆摘下來,,飽滿圓潤,,在手心里熠熠閃爍著紅色的亮光,。
吃一顆,酸酸甜甜,,讓人不由想起愛情的味道,。
我把這次秋收成果帶回家,晾曬在窗前的蓋墊上,,偶爾吃上幾顆,,把瑣瑣碎碎的日子點(diǎn)綴得愈加美好。
有朋友來訪,,一眼看到了酸棗,,訝然說:“你有這個(gè)呀,可以治失眠的,?!?/p>
臨走時(shí),裝包打結(jié),,一股腦兒帶走了,,后來告訴我說,他妻子喝了酸棗泡酒,,失眠居然好了,。
此后,在山里閑逛,,更加留意起酸棗樹,,每次都收獲滿滿。酸棗樹,,不同于家種棗樹,它采摘期長,,即使在立冬前落盡了葉子,,棗子依然懸掛于枝杈上,滴里當(dāng)啷,,甚是好看,。到了冬天,棗子風(fēng)干了,,三顆五顆挑在枝頭,,搖搖晃晃,像暗夜里的燈籠,,散發(fā)著朦朧的紅光,。
劉基詩曰:“雍雍鳴雁來,灼灼酸棗紅,?!边@是正值好年華的棗兒,,豐滿、圓潤,,果肉厚實(shí),,味道酸甜,吃一顆,,味無窮,。
(作者系山東省作協(xié)會員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