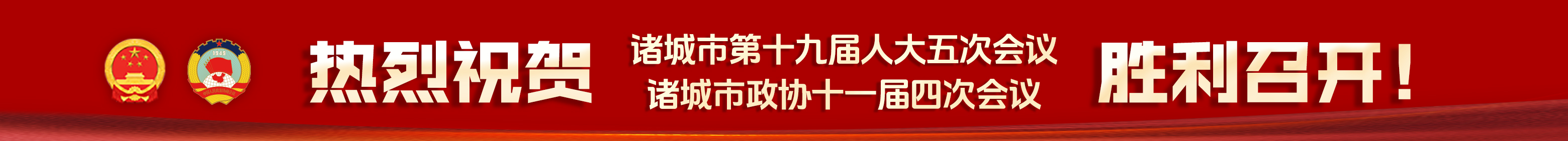我是一直喊娘為孃孃的,,小時(shí)候,,我體弱多病,算命先生說(shuō),,我與娘命里不合,,為了我好養(yǎng)活,娘就故意讓我舍棄了“娘”這個(gè)最親的稱謂,。
姥姥門前唱大戲,,姥姥家是當(dāng)莊,唱茂腔的戲臺(tái)就搭在我村村前一塊高高的空地上,,娘說(shuō)她就是一輩子離不開(kāi)大馬莊的命,。
娘雖未進(jìn)過(guò)一天學(xué)屋門,但政治覺(jué)悟卻絲毫不遜于我,,父母都是黨員,,一九六九年的某日,她在黨旗下莊嚴(yán)地舉起右拳宣誓:我志愿加入中國(guó)共產(chǎn)黨……二O二一年七月一日,,喜逢建黨一百周年,,父母自豪地從社區(qū)干部手中接過(guò)“在黨五十年”紀(jì)念章。那年,,我的拙作《家有黨員》在《今日諸城》頭版刊登,,我以父母為傲。
生產(chǎn)隊(duì)時(shí),,娘是勞動(dòng)積極分子,。田間地頭常常活躍著娘挑水澆地,、送糞揚(yáng)糞,,收割晾曬的忙碌身影,她從不惜力,,在她的人生字典里沒(méi)有“偷懶”二字,,可謂巾幗不讓須眉。一九八三年,,農(nóng)村實(shí)行大包干,,我家分得幾畝麥田。娘忙著耩麥種,、澆麥子,、薅麥蒿,割麥,,脫粒,、揚(yáng)場(chǎng)、曬麥,、歸倉(cāng),。收割完之后接著套種玉米,那時(shí)幾乎沒(méi)有機(jī)械作業(yè),,無(wú)論播種,、鋤草、灌溉,、掰玉米,、剝玉米,都是以人工為主,。娘在坡里勞作,,一個(gè)汗珠摔八瓣,回到家還得洗衣做飯,,陀螺般忙碌,。四十年前,,我村還是產(chǎn)棉區(qū),從栽種,,到挖壟眼,,拿棉花杈,打棉花頭,,滅棉鈴蟲(chóng),,到拾棉花,曬棉花,,去棉點(diǎn)賣棉花,,到最后拔完棉花柴,娘像一臺(tái)永動(dòng)機(jī),,從年頭一直忙到年尾,。爺抽空還得干木匠活掙點(diǎn)碎銀補(bǔ)貼家用,地里的活主要靠娘一人操持,,學(xué)校放假時(shí),,我和妹妹、弟弟象征性地搭把手,,也起不了大作用,。因?yàn)槟锏那诳欤壹业那f稼無(wú)論長(zhǎng)勢(shì)還是收成通常都是村里最好的,。
白天忙碌了一天,,娘又在昏暗的燈光下,戴上頂針,,一針一線地給我們縫補(bǔ)衣服,。我上初中、高中時(shí),,每逢周末,,娘都會(huì)給我烙上一鍋令妹妹垂涎的香噴噴的杠餑餑,炒上滿滿一飯盒油汪汪的咸菜絲,,讓我?guī)У綄W(xué)校去吃,。
一九九五年底我結(jié)婚了,一九九七年兒子出生,,娘又有了新任務(wù),,開(kāi)始忙著幫我?guī)Ш⒆印<s十年后,,娘又去青島給弟弟帶孩子,。那時(shí)弟弟家住六樓,下邊還單獨(dú)有兩層沿街房,娘背著我侄子能輕松爬上八層樓,??春⒆舆@活,不比種幾畝地省力,,不僅忙,,而且擔(dān)是非,唯恐磕著碰著孩子,,天天如履薄冰。好在娘那時(shí)身體挺好,,用她自己的話說(shuō),,從沒(méi)有吃過(guò)一個(gè)藥片,天天干活,,好像從來(lái)不知疲倦,。
十多年前,娘患上了糖尿病,,她開(kāi)始大把大把吃藥,,時(shí)不時(shí)還得去醫(yī)院掛上幾天吊瓶,娘很是無(wú)奈,,常常感嘆自己不中用了,,拖累我們做兒女的。由于病痛的折磨,,眼瞅著娘的身體日趨蒼老羸弱,,我看在眼里,痛在心里,,卻無(wú)力減緩她變老的節(jié)奏,。爺由于十幾年前患下肢股深靜脈血栓,腿腳愈發(fā)不利索,,食品站后那幾畝麥田已然是種不了了,,父母是農(nóng)民,一輩子與土地打交道,,視土地為命根子,,但出于無(wú)奈,只好戀戀不舍地把它交給我二舅,,二舅種地全靠粗放,,擱以前,娘是極看不慣的,,如今也管不了那么多了,。
幾年前,爺娘雖然身體不好,,侍弄個(gè)小菜園還是不在話下的,,但自從染上新冠后,,尤其是爺在前年磕著腰了,走遠(yuǎn)路都得拄拐杖,,娘又在去年動(dòng)了手術(shù),,侍弄小菜園顯然已力不從心了,無(wú)奈之下,,他們不得不把心愛(ài)的小菜園交給三舅,、三妗子打理。以前回老家,,臨回城時(shí),,娘總是把小菜園里的時(shí)令蔬菜、親自腌制的糖醋蒜,、大鍋蒸的老面饅頭裝滿后備箱,,傳遞著對(duì)兒女的那份濃濃愛(ài)意。
在我們老劉家,,除了二孃孃,,做面食板正的就是娘了。無(wú)論是蒸饅頭,、包包子,、烙火燒、包水餃,,還是搟面條,,都相當(dāng)漂亮,她一向看不慣我們做的,,大多親自動(dòng)手,,說(shuō)我們是幫倒忙,不夠生氣的,。這幾年,,身體大不如前了,每次回老家,,包水餃等活都由我和妹妹大包大攬,,皮子厚薄,肉餡咸淡,,娘不再指指點(diǎn)點(diǎn),,任由我們粗制濫造,這也是無(wú)奈之舉吧,。自去年開(kāi)始,,妹妹見(jiàn)娘蒸一鍋饅頭都累得不輕,就勸她以后不要蒸了,買點(diǎn)現(xiàn)成的吧,,自那之后,,每次回老家,妹妹就在城里小家蒸些饅頭,、烀點(diǎn)玉米餅子給父母帶回去,。娘總是無(wú)奈地嘆口氣:真是不中用了,除了吃飯,,什么也干不了了,。
人這一輩子呀,父母和兒女本身就是相向而行的,,起初是越走越近,,總有一天會(huì)擦肩而過(guò),爾后便是漸行漸遠(yuǎn),。人生如同一場(chǎng)戲,前半場(chǎng),,當(dāng)父母的看著兒女在一天天長(zhǎng)大,,滿心歡喜,后半場(chǎng),,兒女眼瞅著父母一天天變老,,滿懷惆悵。某一天,,我突然發(fā)覺(jué)走路帶風(fēng)的娘步履蹣跚了,,不禁鼻子一酸,一種無(wú)助感和椎心之痛頓時(shí)襲來(lái),。
娘的無(wú)奈,,其實(shí)也是我的無(wú)奈呀。
(作者系實(shí)驗(yàn)初中教師)
1 條記錄 1/1 頁(yè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