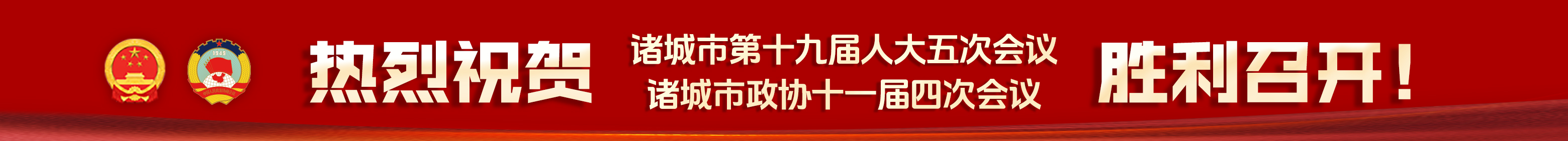孫晉芳
2014年春天,,我的母親又住進了市人民醫(yī)院的肝膽科,,還是因為結石。這個診斷結果讓我們一家人都出乎意料,。早在七年前,,母親因結石把膽囊切除了。膽囊都切除了,,還會再有結石嗎?醫(yī)生說我母親的體質很特殊,,易生成結石,,膽囊雖切除了,但石頭會滯留在膽管里,。我們原以為母親膽囊切除,,就會一生萬事大吉了;也因為我們的疏忽,,從沒想過帶母親到醫(yī)院再查查看看,。沒想到母親還要經(jīng)受這種痛苦。我們全家人又陷入了痛苦不安與提心吊膽中,。
醫(yī)生說沒有好的辦法,,石頭大了,卡在膽管里,,只能手術取出,。但是以后呢?醫(yī)生不敢保證,,因為母親的體質,。母親已經(jīng)七十二歲了,經(jīng)歷過一次大手術,,想起來還心有余悸,,所以,母親堅決不做手術了,。這讓我們躊躇不定,。我從內心里也不愿意母親再遭那個罪,可是看到母親一旦犯病就疼得死去活來的,,心里又忍受不了,。
住院期間,,弟弟打聽到孟疃有個老中醫(yī)專門給病人“貼耳朵”治結石,據(jù)說很有效,。商量來商量去,,最后由父親定奪,父親說出了院就去貼耳朵,。
出了院,,待母親身體稍硬朗了點,弟租了車陪著父親和母親打聽著去了那個老中醫(yī)家,。老中醫(yī)說排石不難,,但得病人配合,因為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,。父親說就是二萬五千里長征也會陪母親走下去,。
根據(jù)中醫(yī)的安排,我母親得五天去一次,,每次都要貼些新的穴位,。每次都要先從家里坐上公交車到城里體育館處,再坐去孟疃的公交車,,下了車再步行大約三里路,,往返一趟七十多公里。去過幾次之后,,我母親抱怨路太遠了,,公交車上又都是硬座,一個來回坐下來,,渾身酸痛,。父親總是笑著說:“想想你疼得打滾滿地爬的時候吧,那滋味難道比坐車還好受,?別一好了瘡疤就忘了疼了,。”有時候,,父親就說:“人家怎么坐車出去旅游來,?你就當是去旅游吧?!备赣H就這樣哄著母親去了一趟又一趟,。
那些日子,父親特別關注的是天氣預報,,每次都根據(jù)天氣預報早做好準備,。但是父親說也得防止天氣預報“失靈”的時候,所以每次出門父親都會帶上草帽,、雨傘和雨披,,還得給母親帶件長袖褂子,,下雨時天涼好穿。每到去貼耳朵的那天,,父親總是早早起床,,燒好熱水,用兩個塑料瓶泡上茶路上喝,。父親特意問了公交車的行車時間,,而每次又生怕不能及時坐上車,總是跟母親一起早早地去等車,。
夏天的天,,后娘的臉。一會兒能把莊稼烤焦,,一會兒又大雨傾盆,。父親陪著母親,按時按點,,風雨無阻,。
我一次次囑咐父親,下了公交車搭出租車去那個村子,,父親總是笑著說:“那么點路,就像散散步,,抬抬腳就到了,。再說在那路邊等輛出租車也很難,有等車的工夫,,還不如走著去,。”我想,,父親說的是事實,,也是不想花錢吧。
以前為上高中的孩子陪讀的時候,,我有過一長段等公交車的經(jīng)歷,,知道等車的滋味。從體育館到孟疃,,車多,,也按點跑,等車并不難,,跑我們村的公交車有時就難等了,,因為偏遠,若沒有乘客或乘客少,,車就懶得跑了,,就會“合并”,,常常要在路邊等上兩三個小時,有時還要白等半天,。
暑假里有一次,,父親說貼藥回來到城里時去龍城買茶葉,我說中午接他們到我家吃飯,。就在他們在龍城買東西時,,大雨嘩嘩地下了起來,地上的雨水四下里流,。我到龍城去接他們,站在龍城大橋上,,我便看到了我的父親母親。在花花綠綠的一片傘和雨衣,、雨披中,,父親穿著暗綠色的雨衣,戴著草帽,,手里提著包,,褲腳挽到小腿下,一高一低,。父親停下,,朝后看,母親在他后邊幾步遠的地方低頭走著,。母親打著傘,,穿著長褲褂,慢慢地走在水里,。近了,,發(fā)現(xiàn)他們的褲子已濕了大半截。
老中醫(yī)用來“貼耳朵”的是自家制的膏藥,,看起來就是剪成比小指甲蓋還小的一片片的白色膠布,。從耳朵開始貼起,漸次到身上其他穴位,。輔助治療的手段(或者稱“藥引子”)是豬蹄子,,清煮,頓頓吃,,每天至少要吃上一個,。煮豬蹄子的活由我父親來做,因為母親不會用電飯鍋,。每次煮三四個,,煮到稀爛,每頓吃的時候需再熱熱鍋。母親一向不喜歡吃油膩東西,,只能沾上點鹽或者醬油的豬蹄要每天吃完一只,,還真不是易事。有時父親將豬蹄端上桌,,母親看著發(fā)呆,,說聞到味就夠了。父親勸母親當藥來吃,,當唐僧肉來吃,。父親還說:“能天天吃上豬蹄也是修來的福分啊?!边@樣,,在父親的督促下,母親整整吃了四個月,。
“貼耳朵”期間還有一項活就是取石,。老中醫(yī)說膽管內的石頭是在藥物的作用下隨糞便排出的,為了驗證療效,,需收集排出的石頭,。老中醫(yī)有他的規(guī)則,那就是患者先用藥,,直到有石頭排出,,再一次性繳上所需費用,每次排出的石頭要集起來,,直到最后連一粒細沙也沒有為止,。母親每次大解時都要把排泄物接在一個塑料盆里,像淘米一樣一遍一遍地淘,,直到最后只剩下了干凈的碎石,待曬干后再收集起來,。我母親對那件事反應太強烈,,做不了,這活又由父親包攬了,。
來回二十四趟,,整整四個月,父親每天都做著他認為理所當然該由他來做的事情,,每天都心平氣和,,每天都無怨無悔。父親每天都是樂呵呵的,,還得像哄孩子似的哄著母親堅持治療下去,。
父親戴著一頂褪色的舊草帽,一手提著一個鼓囊囊的布兜,一手提著水瓶,。人瘦削,,臉黝黑,帽沿下頭發(fā)花白,,手腳古銅色,,青筋暴突。父親邁著不緊不慢的步子,,母親和父親或是并肩,,或是一前一后。這是他們那段日子的生活照,。那畫面永遠定格在我心中,,溫馨、感動又辛酸,。
對待我的母親,,父親堪稱完美。有時候想想,,我實在找不出合適的詞語來形容他,,所有的語言都太膚淺蒼白。
時??吹矫襟w上有人“秀恩愛”,,這樣的“秀”讓我很反感。難道恩愛是可以“秀”出來的嗎,?真正的恩愛是浸透了煙火氣的,,是柴米油鹽中的相依相伴,關心體貼,,是心甘情愿從不計較的付出,。
有一次,跟孩子閑聊,,我說找老公就找像姥爺這樣的男人,。孩子眨巴眨巴眼睛:“但是,姥爺家沒有空調,?!睍r值炎夏。我只好笑笑,,我知道孩子涉世未深,,經(jīng)歷還太少,我希望她以后會明白夫妻之間最需要的是什么,。
(作者系龍源學校教師,,市作家協(xié)會會員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