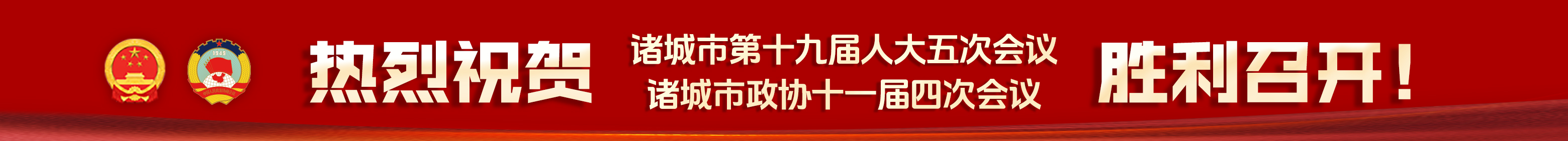郝洪喜
在“以地為本、靠天吃飯”的老家,人們經(jīng)常議論和埋怨老天爺在氣候安排上一年四季不均衡,,都說冬天不如春夏秋豐富多彩,,整個寒冬干干巴巴,缺乏生機,,萬物蕭條,,蒼白死寂。
家鄉(xiāng)父老如此之說自有他們的道理,,但我卻不這樣認(rèn)為,。
因為,我有穿越六十七個冬季隧道的切身體會,,冬季隧道里千姿百態(tài)的景物我都親眼目睹和直接觸摸過,,“冬季韻味”是甜是苦,我有我的感悟和見解,。
因冬韻里,,有溫柔的雪,剛烈的風(fēng),,芳香的臘梅,,晶瑩的冰凌。就其表現(xiàn)形式和內(nèi)容來說,,冬季的韻律和色彩并不單調(diào),。
半個世紀(jì)以前的冬日,呈現(xiàn)在人們面前的自然現(xiàn)象比今天正常得多,。該刮風(fēng)時刮風(fēng),,該下雪時下雪。
那時候,,即使是在冬霧茫茫的日子,,老天爺?shù)难劬σ彩茄┝恋模烫锟实每诟缮嘣?,麥苗凍得渾身打顫,,都看得一清二楚,總能及時送來足夠解渴御寒的救濟品——白雪,,既可當(dāng)水喝,,又能當(dāng)棉被蓋。地上禾苗和地下蜇蟲,,無不因受益匪淺而皆大歡喜,。
寒冷的夜里,,“冬韻”寬闊的胸懷多數(shù)時候是溫暖的。慈母關(guān)愛孩子一般,,太陽一落,,便把北風(fēng)趕走,留下“寧靜”徹夜守護在人們身邊,。
此時此刻,,村前的河,莊后的嶺,,站著的樹,,倒下的草,都在深睡之中,。偶爾發(fā)出一丁點聲響,,那也是正常值夜班的貓頭鷹和蝙蝠等生靈所為。
清晨,,喜鵲和麻雀配合大公雞,,主動當(dāng)起了人們的“報曉志愿者”,它們早早來到天井里那棵大國槐上,,以清脆嘹亮的調(diào)門,,第一時間吹響了喚醒人們起床的號角。
順著房頂煙囪往上爬的裊裊炊煙,,像是沒睡好的樣子,,迫于農(nóng)婦燒火棍的驅(qū)使,強打精神浮在房屋上空慢悠悠地活動著自己的筋骨,,雖是悠閑自得,,卻有些不太情愿。
一排排房舍,,一個個門樓,,都像愛美的大姑娘小媳婦嗜好美容,它們用“冬韻”無償送來的天然雪花膏和護膚霜,,日復(fù)一日地美化著自己的儀容儀表,。仰望它們每天清晨的梳洗打扮,算是一種不錯的審美享受,。
冬季韻味極具個性美,,色調(diào)素雅而濃重,品位超然而灑脫,。與春,、夏、秋三季韻味的轟轟烈烈不同,,大多數(shù)冬的時空里,,充滿清純氣爽的原汁原味,,宛如人們的生活餐桌上上了一盤“清炒山藥根”,白生生,,脆錚錚,,嚼在嘴里樂融融。
當(dāng)時尚小的我,,最喜歡的莫過于冬韻里的特色雪景。別看暴烈的冬風(fēng)刮起來像頭咆哮的獅子,,一旦飄起雪花,,馬上就變得比綿羊還溫順,慢慢悠悠飄灑著,,降落著,,用不了多長時間,天井里就積滿了厚厚一層白銀般的雪,。
我們這些玩童做夢都盼望這一刻的到來,。在孩子們眼里,雪是上蒼送給孩子們的最好禮物,,大到房子,,小到雞鴨,應(yīng)有盡有,,玩啥有啥,。
在我的記憶里,感覺最溫馨的“冬韻”是在我家那盤炕上,。晚上睡覺前,,熱騰騰的火炕上,我們幾個孩子,,圍坐在飛針走線的母親身邊,,墻壁中間小龕里的那盞煤油燈,既映紅了我們,,也照亮了在外間扒蔴的父親,。我們或跪著,或坐著,,或趴著,,嘴里嚼著父親趕集買的“果子麻山(花生餅)”,耳朵里聽著母親“啦瞎話(講故事)”,。母親講得有聲有色,,我們則聽得動情入神。
與世上萬物難找完美一樣,,頗具人性化的冬韻里,,自然也是一分為二,,有和善也有冷酷。冷空氣一來,,誰都有些打怵,。即使躲在屋里,隔著紙糊的窗戶,,也能聽到狼叫一般的風(fēng)吼,,甭說人,就連窗外那棵石榴樹,,都嚇得不停地發(fā)抖,。好在我們堅守在火炕陣地上,易守難攻,,又有父母用身體作掩護,,懼怕心理幾乎為零。相反,,我們越聽越愛聽,,感覺風(fēng)聲就是催眠曲,依偎在母親和父親的懷抱里,,一覺能睡到大天亮,。
天然麗質(zhì)、原汁原味的冬韻,,隨著進城工作而與之握手告別之后,,永遠(yuǎn)留在了可愛的家鄉(xiāng)大地上。事實上,,今天人們感覺和分享到的冬韻某些方面并不差,,隨著農(nóng)村“土暖氣”和城鎮(zhèn)熱力公司的興起,人們在室內(nèi)的舒適程度,,比之過去好了百倍,。
(作者系諸城市實驗中學(xué)退休干部、中國散文學(xué)會會員)